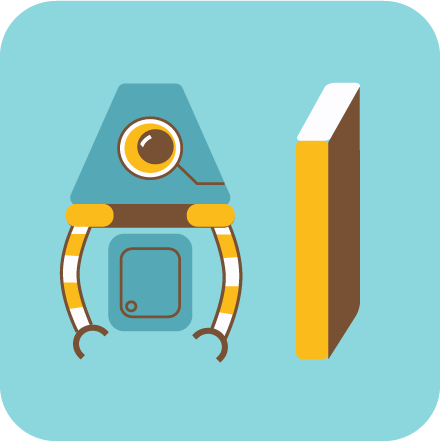谁也不必告别北京
这是一个最无话可说的命题,一场注定面对无数次迟钝、沉默、词不达意、从头再来的写作。你让我辩白事件,观点,正反面,是非题,可以;让我诉说一座山,一场雨,一个人,一段往事,好啊。可写下北京?谁能写下北京? 奔向也好,离别也好,幻想也好,看清也好,你侬我侬也好,斩断情丝也好,每一个想记住北京的过客,只言片语过后,骚动的只有自己。
来过
这是我第二次要离开北京。 第一次是大学毕业,奔赴美国的前夕。最后一个夜晚,我们坐在广场的台阶上直到天亮,后半夜砸了好几个啤酒瓶到广场中央,到现在还欠学校保安一句抱歉。那时我对这座城市完全没有不舍,也没有想过留下来。
这可能是因为那颗野心勃勃的心脏总觉得美国,纽约是一个更大的世界,一个迫不及待奔赴的所在地。也可能是作为一个终日埋头苦读的大学生,我从未感到北京与我有多少关联。我没有去五道口蹦过迪,没有在胡同里骑过自行车,没有站在景山公园眺望过紫禁城,不知道什么季节有怎样的景色,也不认识哪一片街区生活着什么样的人。北京太大了,大到看不见容身之地。

有一次乘着刚开通的 10 号线从中关村漫无目的地坐到了双井。夜幕降临的时候我抬头看着闪闪发光的国贸,忽然觉得从未来过北京。后来那里碰巧成了我第一份实习和第一次自己租房子的地方。每天清晨跟着一大波白领走进写字楼,傍晚站在窗前看汽车尾灯组成的东三环,然后下楼去和同事们吃金湖茶餐厅。在北京读过书,领过工资,谈过恋爱,应该就算来过了吧,我想。
可为什么“来过”如此重要呢 ?前几日去故宫看苏东坡大展,想起妈妈提到过我幼年来逛故宫,刚好赶上关门时间,放起了提醒游客离开的音乐。午门前的广场空无一人,我开始肆意妄为地跳舞,跳了整整半个小时。二十多年过去了,我还依稀记得冬日光影里那个小女孩的身姿,记得那份霸道与自由,记得我来过。
恐怕再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北京一样,能让任何一个人,就算再平庸,再贫穷,再无所依靠,都会产生一种幻梦般的错觉,就是我可以属于这里,就像动物窜入丛林。丛林不在乎任何一只动物,可也不拒绝,也没有分别心。哪怕有天找到了更好的归宿,在别处创造了更好的生活,我们也无法忘记这个慷慨给予过自己无限可能的北京。
告别
离开的原因各不相同,可相同的是,我猜我们都不知道该怎样好好告别。
这一次回来,北京已是秋天。我站在秋光艳阳下,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有点清冷的北方空气。对,北方秋冬季节的气压,是留在记忆深处的某种熟悉。

这才发现,我根本没有好好地看过北京的秋。原来的工作室就在一排排银杏树伫立着的三里屯。每到秋天,我也只会选一两个人少的周末去拍拍照片,鲜有珍惜的心情。总觉得秋天嘛,还会再来的。落叶嘛,可以明年再看。
是要离开的身份创造了距离,是距离 让人得以观看。我想起莲娜姐(晚风说 E71:Jade & 贾莲娜)说,她做项目的时候从来不会一直驻扎在要盖房子的地方。一次次地出发再回来,反而会更多觉知。我们需要这个出发再回来的过程。
于我而言,这则只能算是一种未能尽心沉浸在生活之中的借口。想想唯一未曾落下的,就是各个空间,各种类型的演出,从大剧院中山音乐堂,到蜂巢蓬蒿、school 江湖愚公移山、达达灯笼招待所……为什么?因为足够特别,因为怕错过。对于平凡之物和身边之人的视而不见,也与之相辅相成。
我开玩笑地和二狗(晚风说 E45:Jade & 梁二狗)说,要在跳海办一场告别北京的派对,他说好。可到最后,我也不知道究竟该邀请谁,向谁告别。2020 年够戏剧了,一个人在一座城市的去留,没必要再拉一群演员,添一出戏。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必须要见的人,当场要说的话,要流的眼泪。
说是这么说,可就在一个偶然夜晚,我莫名地在 KTV 包房里哭了三个小时。哭的时候还给住在附近的松乔(晚风说 E33:Jade & 姚松乔)发微信,说你在吗,我离你很近。一个小时后她来了,穿着刚参加完万圣节派对的绿色裙子和斗篷。我说你扮的是什么?她说,一棵树。我想起晚上吃钱粮胡同的 SUSU,还坚持坐在室外,也是为了再去看看院子里的那棵树。
不是没有牵挂,只是不必大张旗鼓。去年我的生日是在招待所被熟悉的朋友和街上捡来的陌生人填满的“特别招待”,而今年则是在跳海酒馆只有默契而至的三五好友的俩仨小时。
只是我不想再喝醉了。曾在别处的酒醉要么是不谙世事,不知分寸,要么是虚情假意,迎合众人。只有在北京,每一次都是掏心掏肺,伤心伤肝。经常喝酒的地方一半都已经消失了。曾经隐藏在三里屯养老社区里的 toy box 并没有倒闭,只是搬到了那里花园,改名叫薛定谔的盒子。可这一改,原来爬到居民楼顶看着闪光的三里屯,在废弃的沙发,假模特和圆形雷达中间上蹿下跳的荒诞乐趣就没有了,再也没有了。

好在我既不寄托希望在未来,更不在过去。每一次,我看见亮马河的水被抽空,北小街的户外座椅被整治,三联书店关门装修,几个月后它们都变成了更美好的样子。家门口的餐厅一个一个倒闭,后来也都开了更好吃的餐厅。我知道有些东西不复再来,有些事差强人意,可也总有些当初以为的辜负,过后会变成深深的祝福。
弥天大梦
如此说来,要生活在北京,还是要懂得如何做梦。房产中介小马哥(晚风说 E77:Jade & 小马哥)说,“总有些北漂想要逃离。你能逃到哪儿去?在北京行,到哪里都行。北京不行,哪里都不行。”我注视着眼前这个从 16 岁的菜农一路走到“四合院一哥”的江湖人物说,可你生存下来了,很多人没有。
其实那并不是我想表达的真正含义。北京不是一场考试,能活下来才是强者。如今这个世界,已经不再是资源如此集中,价值体系如此标准的那个年代了。互联网把一切都分散了,像鸡蛋被打成了蛋花。很多人在 2020 年的离开,不是因为被迫,而是发现了“原来不必须”。
北京也给过我一场弥天大梦,让我觉得离开了这儿,哪里都不能活。
我经历过最疯狂也最荒谬的“黄金年代”。拿着几页 PPT,组个土洋结合的合伙人团队,就有一波一波的投资人追着打钱,比你自己都相信。有胆有识有运气的年轻人,在咖啡馆里车轮战一般地招人,谈合作,谈融资,就这样站在了宇宙中心。再听听旁桌人的谈话,也都是几个亿几个亿的数字,哪一轮哪一轮的估值。
我问郭小寒(晚风说 E79:Jade & 郭小寒),你为什么当初不创业了,又回去写书写稿?她说,可能更想做个创造者。创业的业太大了,况且,所有的业都有“业”。
这些年过去,我把自己的公司关了,对科技行业的关心也渐渐淡漠。身边的同一拨年轻人,有回美国大厂打工的,有被抓进去和流亡海外的,有依然在艰苦创业,只是越来越忍心从公司套现的,也有专心炒股炒币,等待一根阳线改变命运的。
那种上市敲钟的场景也出现了,但好像并不是故事的终结。就在最近一次去酒店大堂等人的时候,我看见了隔壁桌一个一直很欣赏的创业者,如今的上市公司 CEO。他手里握着一杯水,说了两个小时的话一口都没有喝。哪怕只是从侧面远远地看,他眼里的疲惫难熬和紧张用力都是如此明显。我与他唯一一次深聊是几年前从北京去杭州火车上的 5 个多小时。那时他是个刚开始创业的理工男,对自己设计的算法和产品滔滔不绝,满眼都是炙热燃烧的火焰。第二天,他说他围着西湖跑了一整圈。
如今已经上市,有两个女儿的他,还会在开会的间隙绕着西湖跑一整圈吗?我希望会。他是幸运的,是热爱驱使的,是没有被时代裹挟,而恰巧被馈赠的。可若不以结果论英雄,北京也好,时代也好,都只是放大了每个人的欲望,加速了周期,并不会改变那些朴素的常识与规律。
五条人喊,所有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,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。
北京人要的好像从来就不是钱,而是成功,是稀缺资源的占有。钱够花了就行,成功却永远需要比较,需要标准的评价体系。
打工赚钱养家糊口的阶层固然有,能在北京安身立命已经了不起,可他们像是透明的一样,不会是被关注的对象,想成为的人。就算是住在出租屋的北漂,你的梦想也应该是有一天离开这里,再把这里写进传记。一无所有并不会低人一等,有车有房也可能不安无依。你永远可以有更高,更好的目标,不为自己,也要为了家人,为了下一代。
于是我们害怕被落下,害怕被遗忘。于是我们奔赴没完没了的局,重复着言不由衷的假话,拉拢着没有尽头的资源与关系。这一切看起来太自然了,毕竟这是北京。
那也没有关系。什么样的人选择什么样的生活,一个人生阶段就该是那个阶段的样子。只不过,青春就这么过去了。为了在这个评价体系里得以生存,得以赢,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。新的世界要靠在乎的人去创造。显然,我们尚未迎来那个”更好的世界”。
大梦初醒,我知道是自己变了。
都是生机,都有趣
北京有一个叫四得的公园对我来说意义非凡,它象征着四季、生命、自然。整圈跑道只有一公里,花园里一应俱全,植物顺应季节的变化次第绽放,次第衰落。无论春夏秋冬,都有一串串长跑者挺胸抬头地经过,都有孩子对着树叶的惊奇,老人吹拉弹唱的生机。
这一次,银杏和银杏果金灿灿地铺满了山坡,后园新种了一大片格桑花,正中央的莲蓬和芦苇已经不见了。我顺势躺到有阳光的长椅上,闭上眼睡了。
睡醒的那个瞬间,回忆一股脑涌上来,让人恍然不知身在何年何月何时。第一次做产检等结果的时候我也是在这,从眼前的跑者身上感受到强大的生命力,顷刻有了对孕育生命的信心。后来女儿出生了,我总是带她来。只要答应上完足球课去坐游乐场的旋转木马,她就可以自己走,不让抱。再后来她又长大了一点,会主动脱了鞋踩上草地,边用脚趾挤压小草边说,抱抱你,抱抱你。

北京的所有公园都有围墙,所有草地都不能躺。在保安看见之前抓紧机会光脚踩草坪,那感觉就像裸奔。后来我发现宝格丽酒店室外区域的草坪是可以的,哪怕没有消费。于是常在周末清晨躺在那看书晒太阳,算得上是比吃得上旁边的米其林二星新荣记更奢侈的事情。
有人觉得亮马河畔的三里屯就是北京,有人觉得胡同里的四合院才是,而对于另一些人,是最高最高的那栋写字楼。北京永远有更深邃,更高不可攀的一面,也有残酷的,抹掉滤镜后的现实。
这个现实就是,所有对北京的巨大幻想,就是对自己的幻想。若有天破灭,那我究竟是谁?
出发再回来,忘记再观看,我才发现所有关于北京的故事,和故事背后对北京的看清,都不过是自导自演。我一直沉溺在狭小的圈子里,以为那就是世界。我遇到的人群,只是人海茫茫中的一小撮,他们不能代表谁。我所过的生活,也只是亲身经历的的个体选择,仅仅属于我自己。我既不需要趋同于人,也不需要遗世独立,更不必强迫自己理解所有人,或被所有人理解。这个世界不依照地域,人种,阶级来划分,也不遵从任何人为定义。宇宙没有中心。
黄章晋(晚风说 E72:Jade & 黄章晋)说,未来的媒体趋势是个人化,超级头部再不会出现。我问他,那你怎么定义你自己的属性?他说,老一代北京人吧,五环内的那种。能吸引的粉丝,也是同一种人。
我们都被原子化了。我们所相信的,追随的,也各不相同。集体记忆还会有,可不会再是十几亿人一起看春晚的那种。我翻看过杨炸炸(晚风说 E53:Jade & 杨炸炸)十年前一举成名的摄影集《爱在北京》,可我没看到北京,只看到一个个鲜活的个体,和炸炸本人的眼睛。
于是当我再次走在路上,就看见了完全不一样的景象,遇见了完全不同的人。世界只是你关心的那样,其他的揣测都毫无意义。
我喜欢看胡同里的大爷大妈热心肠又凶巴巴的样子,喜欢看他们脸上的傲气。喜欢听自行车铃铛当街而过的声响。喜欢看大小咖啡门口的乒乓球台边,两个女孩用捡狗屎器捡球。喜欢经过五道营 school 的时候,门口的保安扬眉吐气地说,票卖没了,都没了,晚点再来吧。


都是生机。都有趣。
我甚至有点喜欢上堵车,喜欢等位和排队,喜欢真实的丑陋和不完美的真实。退掉工作室后,每次录播客我只能闯进嘉宾的家里。可那也成了一种借口,得以观看他人的生活。
福禄寿三姐妹(晚风说 E70:Jade & 豆豆(福禄寿))的公寓里供养着三只猫主子,混乱的难以下脚。她们回到家就黑白颠倒,忘记时间,还有好多歌想要写。有一个深夜她们在家门口的立交桥下骑车,遇到一个突然对着长空一声狂吼的中年男人,振聋发聩,惊心动魄,就想把他写下来。他有什么苦?什么故事?谁会去留意,会为他写首歌?
莫非老师(晚风说 E80:Jade & 莫非)一出门就扛起相机,一回家就扎进书房。书房里全都是已经绝版的七八十年代老书。桌上那本维特根斯坦借给过海子,后来海子自杀了,他重新买了一本。我俩从天亮一直聊到天黑,没有人记得开灯,直到他抽烟的侧脸成为一道剪影。他扭头看着窗外楼下的树说,这个是山楂树,很多人都不知道,这个是山楂树。
我照旧去找榕杉(晚风说 E26:Jade & 榕杉)练瑜伽,找小菀(晚风说 E68:Jade & 小莞)跳舞。我吃了赵濛(晚风说 E78:Jade & 赵濛)烤的面包,听了他弹钢琴。
原来有那么多人在专心致志,心满意足地做着自己的事情。他们想守住的不是一所房子,一座城市,某个圈子,某种意义。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,他们只是恰好在北京。
谁也不必告别北京
最接近临别场面的一次,是开车一个多小时到了名叫“鬼笑石”的山坡。朋友说那是一个车可以开上山的观景台,往下看是全北京的夜景,往上看是星星。我依稀认出了长安街,认出了国贸三期,分清了东南西北。我没有觉得有多漂亮,多迷人,倒是好奇迎面而来的都是谁,为什么会在凌晨1点来看夜景。

如果这样的一块石头,来了就算来过,走了就算别过,那迎接的,告别的究竟为何?怎样才算来过北京?
有了房有了车?
打过工创过业?
组建家庭生儿育女?
有很多朋友,被经常念起?
哪里都认识,哪里都曾去?
学历?户口?关系?记忆?
……
这算证据吗?这算什么证据?
告别的心无非也是证明来过的心。可如果什么都不需要证明,那就谁也不必告别北京。
北京只是以比人情世故更长久,比天地自然更短暂的方式存在在那,任你来任你去。她的每一次变化,大到雾霾从无到有,小到门口咖啡店倒闭,都在以一种既友善又残酷的方式询问你,让你看看你自己。你所沉迷的, 嫌厌的,费尽心机的,心安理得的,喜新厌旧的,故技重施的,都是你给世界的,不是世界给你。
你可以告别养过的每一株植物,跑过的每一条路线。你可以告别春天的垂杨柳,秋天的银杏叶,有 12 条车道的长安街。
灯一亮,台下的人转身离开,台上的人鞠躬谢幕。司机说车上的温度合适吗,你关了车门说谢谢。归乡的鸟啊,分手的人,哪会真的再见。
你披荆斩棘又如履薄冰,不过是想赤诚地来,坦然地去。你用力地爱,用力地恨,暗搓搓盼望着“终有一天”的大结局。
你可以告别每一个万里无云的艳阳天,每一轮仰头凝视过的满月。但更多的时候,你什么也看不见,什么也听不见。你自以为是,满口胡言,挥霍了所有侥幸,消磨了所有信念。
胆量、企图、希望、习惯、安全感、虚荣心……一切对生活的雄心壮志都在这里。一切自欺欺人的谎言也在这里。你走吧,走了也没改变。
我就这么又一次上路了,仓促地,狠心地。我不再在乎去哪里,哪里都一样了。不请自来,不告而别,要去哪,遇见谁,以怎样的方式度过人生,都是偶然的,没有征兆,没有原因。再亲密,再眷恋,我们都只是互送一程的关系。我也不再怕告别了。告别了这个最爱的城市,我就可以告别任何地方,告别任何一个时空的自己。
快走的那个晚上,TT(晚风说 E6:Jade & TT)请我喝酒,我说哪。她说就在家楼下的马路边。她穿着睡衣,拎着从超市买来的两瓶长相思,从隔壁酒吧点了水烟,点了一大堆烧烤外卖席地而坐。我们一起去过的地方那么多,可好像只有这个马路边,配得上如此宿命的场面。她没有问我什么,只是端起酒瓶说,我为你骄傲。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她口中的骄傲是什么意思。而就在转天,我得知搬到上海几个月的易石(晚风说 E21:Jade & 易石)要搬回北京。我隔着屏幕会心一笑,好像并不需要知道为什么。

走了的人,无论呆过多久,离开多久,还是会说“过几天我要回北京”。他们回去看演出,逛街,下馆子,办签证,见朋友,卖房子,假结婚……这里可能给不了我们优美,廉价,宜居的生活,给不了绝对的公平和相对的正义,可她给了每一个孤独的个体最深刻的理解,和最无条件的接纳。
有的时候我想起《恋爱的犀牛》里那几句台词,“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,冰冷的啤酒,带着阳光味道的衬衫,日复一日的梦想。”我觉得那仿佛是在说北京,正如剧中那个无法被占有的明明。
北京是所有人的。谁也不必告别北京。